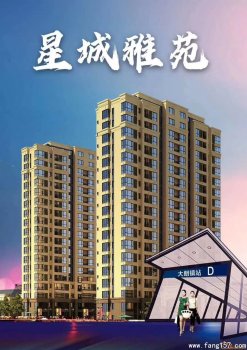▲《我们深圳》丛书已出版11种,包括《杨争光:文字岁月》《远渡加勒比》《寻找罗定朝》《她的老街:1979-1983》《血脉》《沙井蚝》《白石洲》《寻找光明记忆》《华强北魔方:寻路》《华强北魔方:硅洲》。(资料图片)


▲钱汉江、钱飞鸣合著的《华强北魔方》包括上册《寻路》与下册《硅洲》两本。 (资料图片)

▲《歌声起处: 深圳流行音乐四十年》 王俊 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8年4月
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推出首部深圳人文大型文库《我们深圳》,记录关于深圳的一切。7月20日下午3点,《我们深圳》丛书读者见面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广东馆活动区举行,杨争光、谢湘南、陈瑛、远人、阮飞宇、吴晓雅将来到现场,讲述他们关于深圳的城市记忆。
从“深圳文库”到“我们深圳”
几年前,深圳人胡洪侠回了趟阔别多年的故乡,故园依旧在,乡人已不识。
胡洪侠已经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。这些年间,他从未放弃叶落归根,深圳,不是他曾经梦想的终老之地。
而这趟故园之旅,改变了他的想法。
原来,家园和家园感不是一回事。当故乡再也回不去,那座他为之奋斗与它共享荣光,最终给了他深深的家园感和归属感的城市,又怎能不认识它的每一寸土地?了解它的地理人文,熟知它的历史文化?
从那时起,他萌生了要给深圳编撰一套大型丛书的想法。
2014年,胡洪侠给深圳市提交了一份详细方案,提出要启动编撰大型出版工程“深圳文库”。在他看来,每一座城市都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书,深圳尤应如此。这里不仅有几千年前的咸头岭文化、几十座见证了客家人繁荣兴衰的围屋、久经历史风雨的深圳老墟、虔贞女校、南头古城,更有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留下的大量珍贵文献、学术成果、文学作品,某种程度上,它们不仅合成了一部深圳的改革开放史,同时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。
编撰“深圳文库”的想法,市里非常重视,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论证会。然而涉及投资、征集文献,困难重重。编撰如此大规模的出版工程,似乎,条件仍未成熟。不得已,这一动议被暂时搁置。
2015年,胡洪侠到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之后,经过多次论证,决定缩小范围,绕开难度较高的文献整理,先从相对容易操作的非虚构做起。
就这样,一套名为“我们深圳”的丛书,在这一年年底正式出笼了。
葆拉的故事打开另一扇窗
2012年,前NBC高管和通用电器公司副总裁葆拉·威廉斯·麦迪逊回到深圳,寻找自己客家籍外祖父塞缪尔·罗(中文名“罗定朝”)的新闻,就引起了岳鸿雁的注意。
那时,岳鸿雁还不是“我们深圳”丛书的责编。但这个传奇的故事,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。
1906年,龙岗的客家人罗定朝背井离乡,远赴牙买加谋生,期间结识牙买加姑娘生下葆拉的母亲,葆拉母亲3岁时,随其母返回家乡,罗定朝后因生意失败返回中国,自此,葆拉母亲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,带着遗憾离世。葆拉自小感受母亲缺失父爱的忧伤和找寻家人的渴望,在她2012年退休后,将找寻母亲在中国的亲人作为首要人生目标,从此开启了一段跨越地理、种族和文化的寻根故事。
借助古老的文献、数码资讯,以及牙买加华人社团的帮助,葆拉终于在深圳找到了300多位失散多年的亲戚,在罗定朝旧居、龙岗客家围屋鹤湖新居实现了罗定朝所传8个家庭100多人最完整的一次相聚。
“我们深圳”丛书启动之后,岳鸿雁第一时间想起葆拉的故事。2016年3月,她通过客家文化研究学者刘丽川、张卫东夫妇联系到葆拉,请她把这段寻亲经历记录下来,并参与翻译,这就是后来的《寻找罗定朝:从哈莱姆、牙买加到中国》。与此同时,又邀请葆拉的表弟罗敏军撰写《远渡加勒比:彼岸的祖父》,讲述当代深圳新移民的前辈——那些客家原住民,在近代远赴美洲、开基创业的奋斗历程。
如果说《寻找罗定朝》讲述了一段源自深圳龙岗客家围屋鹤湖新居的百年传奇,《远渡加勒比》就是一部客家先民海外垦荒拓殖的真实历史。而这两本书合起来,更是中国宗族文化和全球文化融合一个难得的文化标本。
深圳被贴上“移民城市”的标签,是最近40年的事。葆拉的故事却给我们打开另一扇窗——从垦荒、移民,到寻根、回归,历史早已有之,历史还将不断重复。
打捞本土历史有多重要
在进入深圳光明新区文化发展中心之前,陈瑛供职于光明新区图书馆,正打算进一步丰富光明新区图书馆的区域特色文献资源。更早之前,她在湖南长沙做过城市记忆方面的工作。作为研究馆员的她,对光明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“现在的光明就像30年前的罗湖和福田,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,许多老建筑、老街巷、老传统迅速消逝,城市记忆的传承与保护任重而道远。”虽然光明远在深圳与东莞接壤的地方,发展比原特区内的福田、罗湖晚很多,但陈瑛已感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,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保护的急迫性。
“如果不尽早收集这份记忆,那些世代生活在这里的‘土著’,会被迅速冲散在新的城市里。而我们新移民,也难以找到城市的根。”2014年年中,“寻找光明记忆”项目启动,陈瑛和她的项目组近百次走进社区旧村,采访约200人,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,试图从那些本土人的氏族源流、古旧的建筑、传统的习俗、特色的美食中,寻找专属于光明这座小城的历史记忆。
经过几年的寻访,由陈瑛主编的《寻找光明记忆:新城旧事》作为“我们深圳”丛书的一种,在2017年底面世了。这是“我们深圳”对深圳各区历史挖掘的开始,未来,还将一个区一个区地“打捞”下去。
对本土历史的“打捞”有多重要?胡洪侠觉得,非常重要,“你不了解这座城市,怎么会有家园感?”
在他看来,很多人在深圳生活,过的却是“非深圳生活”。他们吃的是麦当劳,穿的是CK,挎的是LV,随着全球化的入侵,每个人生活中的“共性”越来越多,却忽略了脚下这片土地。“我们深圳”丛书要打捞的,就是行将消逝的本土记忆,它要给深圳人留下一份“故园家底”。
深圳人的历史感格外强
1982年,钱汉江来到《深圳特区报》,成为特区第一代记者。那是纸媒的黄金年代,跑工业线的钱汉江,亲眼见证了赛格集团的诞生,经历过“敢为天下先”观念被提炼出来的全过程,成为深圳工业初创期的重要记录者。
1994年,钱飞鸣追随父亲的脚步,在《深圳商报》做了一名科技记者。他最早报道了深圳“创客”,他的评论促成了“深圳国际低碳城”的诞生,关于深圳经济方面的成长,他一直做着持续的观察和记录。
2018年,钱家父子合著的《华强北魔方》(上册《寻路》,下册《硅洲》)面世。这两代深圳记者,用自己的亲历记录了深圳电子产业40年的变迁,也借助“魔方华强北”写下了一部深圳创新志。
撰写过程中,钱飞鸣深刻地感受到,深圳人身上有一种其他地方少见的责任感、担当感。这在赛格集团创始人、原董事长、深圳电子工业和“华强北电子一条街”的主要奠基人马福元的身上,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不少人的记忆里,上世纪改革开放初的80年代,是一个火红的年代,激情燃烧的年代。马福元当然也不只满足于把赛格办成一家造福一方的企业,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,就是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。
用赛格这样一个“支点”,撬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“地球”——这样的野心,在今天看来都极具魄力。可那个年代的深圳人敢梦,敢想、敢做、敢去承担。


上一篇:车范根在深圳圆了20年青训梦
下一篇:上半年深圳消费者投诉 互联网和通信服务最闹心
- 【 光明区 】光明独立红本房【智荟天地】相当于16000一平
- 【 光明区 】光明13栋花园【凤凰城公寓】地铁口200米送精装修
- 【 光明区 】公明塘尾【塘尾学府】单间首付7万起、带精装交房
- 【 光明区 】光明6号线地铁旁【科学城首府】科学公园站200米带豪装
- 【 虎门小产权房 】【虎门华庭】3房29.9.两房18.8.三大栋 虎门最低价
- 【 虎门小产权房 】【水岸新都】限时特惠 一口价房源 享有3层停车场 户户安装天然气
- 【 虎门小产权房 】【东湖雅苑】2480任选 不分楼层 不分大小 一线湖景房
- 【 虎门小产权房 】【鹏德豪苑】 万科旁三层 1:1.2停车位花园小区 精品豪宅现房
- 【 虎门小产权房 】【滨海湾●悦海城】与华润置地为邻 真正公园里的家.带1:1停车场
- 【 龙华区 】6栋花园21层、带煤气管道、停车场